《华为访谈录》- 田涛
2025 年读完的第 4 本书
华为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?任正非是一个怎样的人?关于这两个问题,有各种各样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解答,唯独华为人自己的声音不是很多。
华为公司顾问田涛在2013年至2019年6年时间内,对华为上至高层下至普通员工共几百人进行了访谈,《华为访谈录》是这些访谈的第一部结集成果。
通过这些华为人不设防的侃侃而谈,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华为,包括它是怎么起家的,它的第一桶金,它的独特的组织文化,它的永续折腾的变革史,它的自我批判精神,它的激进的研发战略和充满英雄气质的市场开拓、冒险与征服、血与泪和歌与酒的奋斗,尤其是它是怎么一步步从一无所有、“四大皆空”(无背景、无资本、无技术、无人才)走到全球领先地位的曲折历程,还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任正非,他有着什么样的人格特质、领导风格、独特个性和优缺点等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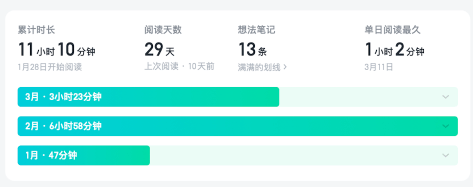
访谈2 吕克
公司一直奉行民主讨论、权威决策。但我们现在民主讨论有过之,权威决策犹不及。从华为的文化角度来看,走其他任何一条变革之路,只要坚持下去都可以,只要内心真正坚持,就一定走得通,变革要有耐心和决心,最怕的是犹豫摇摆。我到一线访谈,发现其实所有的一线主管都有各自的立场,但都表达了一个观点:公司决定怎么走就怎么走,不要再摇摆,摇摆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做了。所以我觉得组织变革这方面,公司是要听大家意见,但听完大家意见后一定要有权威决策的机制。不可能有一个方案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和兼顾所有人的利益,只能百害之中取其轻,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
业界的方法怎么走呢?譬如你现在一个12人的研发团队,按照配置模型去配置,一个项目经理、一个技术经理、两到三名高级工程师,三到四名普通工程师,一到两名助理工程师,就这样一个结构,每个岗位的工程师就拿相应岗位的待遇,就是序列待遇。这个序列待遇每年跟着业界增长,在业界保持竞争力,最后优秀的人能升上去,普通的人干烦了可以横向流动。
对研发你最后要看的是什么?不是速度,不是玩命的加班,其实从产出角度本质来看,是一个时间和质量平衡的问题。一个组织,要有一些有经验的人,也要有有冲劲的人。
华为过去的成功其实在于我们经营管理模式或HR模式跟业务模式完全匹配。比如更低的成本,我们在中国,这种人力成本很低,而工作有更快的速度,我们玩命地干,保证好的质量,而且我们不断地投入人力,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三个优势做出来,这三个优势刚好是跟随者最大的优势,所以我们成功了。
访谈3 江西生 (第二次访谈)
我认识一个活佛,他属于藏传佛教,挺厉害的,来自中国最大的佛学院色达五明佛学院,那里有很多学生。他对我说过他们佛学院的院长是怎么产生的。他们有5个大喇嘛,每人执掌一年,执掌一年中每人都带一个人,这5个人轮一圈后就退了,他们带的那几个人上来。上来的几个人又开始轮一圈,他们又带人……就这样循环下去。这个挺有意思的,他们也是轮值。
人性是跟利益结合的,有利益的时候,就更扭曲一点。如果利益配合得很好,那组织不合理的一些地方可以得到弥补,可以容忍;如果利益跟不上,就会有很大的问题。为什么很多企业很快就分崩离析?就是两者必须要有个结合,它们没有做好。
在澳大利亚我们做得比较好,董事会有3个外国人,我们公司有4个人。但董事长是外国人来做的,而且主要听他们的,因为他们发挥很多积极作用。以前不太能理解,但现在来看是很放心的。另外,4∶3这个比例是我们设计的,真的有风险的时候保险嘛。我认为,最关键的还是找人,找对合适的人,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层次不是太高,找的人不合适,他也会给你搅和乱的。在国外,董事不一定代表股东,而是站在职业角度,最主要是依法,他要遵守法律。其次,他是站在公司发展的角度,站在他自己理解的角度。
访谈4 卢赣平
田涛:这是对华为很重大的挑战。早期,华为更多的是面向现实需求,去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,但10年后你是面向未来投资。面对未来投资,是不是有很多不确定性? 卢赣平:对。 田涛: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? 卢赣平:我觉得应该搞些人去思考这个,研究这个。要开放思想、开放合作,大胆创新和尝试,把思想、创新、尝试、样品化、产品化的短、中、长期结合起来,不能在投入上卡得太死。
搞IPD是很好的。因为早期我们就是游击队那套做法,怎么去把产品研发与市场、财务挂起来,这个是IPD要解决的一部分问题。另外一部分是,IPD还有更多研发管理的东西。研发里面,我觉得两个方面都很重要,一个是研发的创新,另一个是研发的管理。研发管理就是对知识或技术有效管理的应用,像拼积木一样,你知道箱子里都有啥,当你需要拼个东西时,把箱子里的零件拿出来,就能低成本、快速地把它拼起来。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,我理解它叫研发管理或技术管理。
IPD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,第二个方面在早期是比较弱的,前一点财务的投入、测算在形式上已经走起来了,但实质上它有没有真的做到?比如说当年投的一个产品,在市场上的赢利、收益,跟决策时对比,会有个动态的变化过程,这个过程是不是去管理了,以便更有效地去瞄准市场,更好地做决策?这是个学习改进的过程,这条路要走好,不要形式化。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形式化了,搞个决策准备一堆材料,然后十来个人一听,很多人也听不太明白,就去走形式化。形式化绝对害死人。
访谈6 陈珠芳
后来我是怎么把这个核心价值观变成了高绩效的文化了呢?其中就谈了7个问题。经营企业不是谈灰度、谈妥协吗?在哪里有灰度?矛盾在哪里?主要矛盾是什么?我就按照我过去学的知识梳理出,企业面对的主要矛盾有7个。
第一个是外部世界内部化。经营企业,要活下来,社会需求才是企业活下来的理由,没有社会需求就没有活下来的份儿。那么经营企业,产品的战略,各种各样的战略、定位,到底是靠外部导向,还是内部员工自己想出来的?是创造机会还是抓住机会?其实两者都有。有时候内部没有思路,没有内涵,客户讲100遍你都听不懂,外部世界进不了内部,不可能变成你的产品去适应客户。所以外部世界要内部化,内部没有内涵是不可以的。那怎么样使自己的内涵丰富起来?这是一个矛盾。这个讲起来要很长时间,要不一个课程怎么搞几个小时呢?
第二个是,流程、制度的稳定性、严肃性、规范性与它的灵活性这对矛盾怎么去解决。严肃性之下如何发现例外?有例外的时候应该怎么做?怎么样才能修正原来已有的流程?这是第二个思路,叫作规范性与灵活性(亦叫作“制定规则,发现例外”)。
第三个是,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。创造财富不可能没有集体主义,没有集体主义创造不了财富,当下的财富肯定不能靠单打独斗创造出来。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少数的技能活、艺术靠个人,靠自由职业者,但是作为一个组织来讲,没有集体主义是不行的。但是作为一个企业,没有个体的差异,不保持个体的独立性,每个人都是从众,也没有创造性。所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、个体差异又怎么兼容?
第四个,在人和组织管理里面,一条供应链里面,华为的客户、客户的客户、华为的供应商、供应商的供应商,这条生命链如何做到多赢?其他就是组织的管理、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管理、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管理,这些矛盾。
还有一个,对成就者的认定。哪些是奉献者,你怎么认定。对这种认定,到底一个人在企业里面的成功、获得的回报,是组织赋予你的,还是个人努力挣来的,这也是一对矛盾。其中我就谈了有一条,老板在《致新员工词》里的最后一段,是很牛气的,民族精神很厉害,我说:“哎哟,华为现在是国际化企业,有那么多国际化的员工,还是民族氛围那么重行吗?”我就想改这一段。但是我没敢跟老板讲,我就跟人力资源部讲,说这一段是不是还要改一下。老板说,改什么?我就说那不用改了。
访谈8 李建国
- 我对制造总裁岗位总结了几点:一是“大志小行”,“大志”就是志向要远大,华为制造业务要成为ICT行业的“丰田”,要成为制造业的标杆;“小行”就是要在关键的小事上做好,比如关键的质量控制点、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、员工关系;二是“知行合一”,我坚持每个星期都去一次生产现场(含外包厂现场),每个月亲自召开一次质量会议,14年从来没有松懈过,始终都是亲自抓质量;三是“静水潜流,持续改进”,把华为核心价值观中的自我批判,在制造部诠释为推行全员持续改进,每天都要比前一天做得更好。
访谈12 吕克 (第二次访谈)
所以我认为机制是有生命周期的,组织一定要保持不断审视过去的机制并优化的能力,与时俱进地改进。
有时自己也感到委屈,就找陈珠芳老师沟通,她说,做人力资源的人,就是陷在利益旋涡中的人,要学会“无我”精神,只要你相信你是对的,你就得承受下来,敢于坚持下去。这些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。
